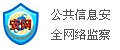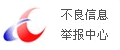| 家教冯老师的文章列表 |
|---|
游三峡(三)白帝城 [随笔杂谈]
发表于:2012-11-08 阅读:13次
中午时分,燕山号打了声标准的男中音,“嘟——嘟——”,做纤夫样喊着号子,从巫山港启程了。 船拨着被太阳煮沸的江水,老水牛般向上游游去。 两个小时后,到了白帝城。 站在江上望白帝城,比想像的小得多,整个城就是一个小岛,有点像大馒头,或者说是中华鲟吹出的绿泡泡。不过,正如人不能以高矮论才能,物质不能以体积论分量,小小的白帝城从公孙述的膨胀的野心中走来,从刘备的幽幽冥想中走来,从李白的疾箭般的船中走来,从古战场的硝烟中走来,凝着厚重的历史,携着动人的故事,让人瞻仰和凝思。 历史上,白帝城三面环水,雄踞水陆要津,可以想象有多少贪婪的眼睛觊觎过,多少烁光的刀戟嗜血过。白帝城既是催化剂又是发酵剂,既是伤感的《二泉映月》,又是亢奋的《十里埋伏》。它是坦荡的戈壁,是汹涌的大海,飞奔的战马飞溅着多少冲天豪气,疾驰的战船闪掠着多少英姿胆影。白帝城是他们窥视天下的高塔,是他们掘闸漫水的堤坝。他们车轮样辗过宫殿的甬道,辗过雾腾腾的历史。就像这长江水冲刷着泥沙,冲刷着硬棱棱的峭壁。 这就是男人!男人是踏着哒哒的铁蹄叩世的,是擂着咚咚的战鼓腾起的。男人就该是一跃千丈的骐骥,是仰天长啸的烈狮,是俯冲掠地的雄鹰。是男人就该做栋梁撑起一方砖瓦,做楫桨推动一艘轮船。公孙述是伟男人,刘备是伟男人,诸葛亮是伟男人,李白是伟男人!正是这些伟男人,这块土地才有了铮铮铁骨,才不成被人类的洪水冲刷掉的软泥巴。 白帝城,你实在是长江耸起的饱满的乳房啊! 临江的岸边伫立着一个碑子,写着三个大字:白帝城。其实,是不用写你的名字的。葱郁的树掩不了刀光剑影,远处的夔门拱月般把你烘托成灼目的绿太阳,滚滚的江水酣畅淋漓的讲述着你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,你的上空蜃楼出惊心动魄萦心绕肺的场面。你的名字是写在人们心中的。 若隐若现的飞檐楼阁闪烁绿荫中,如闪烁的历史,如夜空闪烁的星星。闪烁的还有亭阁中标点样的游人。 船往前行,渐渐的,飞架南北的一桥展现在眼前。这桥,一手拉着魁梧的楼房,一手牵着白帝城。桥,成了风筝线,白帝城摇曳在奉节的上空,奉节摇曳在白帝城的上空。 拐过个小弯,绕了个圈,燕山号进了奉节港。我们换乘中巴,到白帝城。 白帝城,我就要与你最亲密的接触了!公孙述,我就要一睹你的容颜了。诸葛亮我就要聆听你的智慧了。李白,我就要沐浴你的豪气了。 下了车,我走在最前面。我要成白帝城你第一个瞻仰者,第一个洗礼者。我要读透你每一个枝叶,每一个台阶,每一片砖瓦。 可不想一个小插曲影响了我。太短的时间使我只能像飞燕掠水,我瞻仰的目光只能轻点白帝城。可我此行不很遗憾,我已经读懂了你的一个内涵。你用江水咆哮的力量在我的脑叶上镌刻了大大的词,叫巍峨,叫挺拔,叫不屈不挠。 |
游三峡(二) [随笔杂谈]
发表于:2012-11-08 阅读:10次
燕山号把我们驮进了黑夜,又把我们从黑夜里驮了出来。当黑夜被这艘坚毅的船划进深水时,刀削的山又呆如木鸡的立在水两边,茫然的注视着我们了。 这,已是七月二日了。 虽是清晨,却不清爽,热量在水气里涌动,水汽像被蒸馏过,刚从火苗里逸出。 早饭,我们是泡在汗里吃的,空调狠劲儿的翻着舌头吐着凉风,可整个餐厅还如孵箱,我们的脑门和身子没孵出鸭苗,却孵出了不少盐水。 船在我们吃饭的当儿,绅士般踱进了巫山港。 下了船,一拨人换乘小船去游小三峡、小小三峡,振伟,秀峰,广超我们四人则登上了巫山县城。 爬上长长的堤坝,穿过宽敞高大很是恢宏有气势的候船厅,就是一条沿江柏油路,稀疏的行道树被斩下头,齐齐的颈口萌出一簇嫩毛发。毛发是嫩的,柏油马路也是嫩的,称得上嫩的还有路边怕毒日而窝在篷下的一辆辆四轮车。 第一次见这种车,我们几个蹲下来研究讨论了好一会儿。车是脚力的,左右两座,各有脚踏,想必是情侣用来宵夜闲游觅情趣的,姑且就叫它情侣车吧。可以想象,眉月眯眼,月色朦胧,清辉柔抚,霓虹闪彩,一对情侣在情侣车上,或依偎入怀,车悠悠行,如曲入平板溪绕卵石;或你唱我和,你仰笑我俯乐,车也跟着摇曳,轮也沙沙有声,若玉指弹弦水涡旋铃。这该是巫山县城唯这条道上才有的风景吧。更添风景内容的,是长江水流呜呜,耀着斑斓的水鳞片,像暮春姹紫嫣红的花瓣撒满江面,游动的船灯是还在盛开的牡丹和大丽花,闪烁的航标是江水的眼睛。这神秘在黑夜里的长江偎着这情侣车摇沸的沿江大道,该是又一对绝配的情侣。——我想应该是的。 “爬上县城看看吧?”振伟提议。 我收住思绪的脚,也跟了去。 仰望县城,一排楼房错落有致的昂然挺立在至高处,鸟瞰伏深的长江,鸟瞰小不点的我们。不知怎的,我突然想起当年陕北清涧县山上傲然独立的毛泽东。这一栋栋楼房也在吟诵“沁园春”歌词?也在唱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? 我加快步伐,想尽快再贴近那伟岸的英姿,更深读那铮铮豪气。 楼房终于在我们热汗裹着的喘息里立在脚边了,可怎么也没想到后面又是一层矗立的楼房,过眼前的一块儿平地又是宽宽长长的阶梯! 继续上爬!我们四个真有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。 还是意外的在阶梯消失的地方,又往天上搭上高高的阶梯,这层楼房的肩上又伫立另一层楼房。这些楼房!是在做猴子们摘桃吧,是在摘天上的仙桃吗?仙桃不会有的,楼房们倒会摘到夜明珠般的星星。 回首望,音阶般的阶梯把一排排的楼房缀成条形冰糖葫芦,楼房摩肩继踵,是饴糖多把它们粘在了一起。他们站成了合唱队,面对长江,面对长江傍依的山峰。这镶着工人们厚茧的台阶,是伴奏的钢琴,巫山人,还有我们,是弹键的手指;水上的轮船是拉拉队。 楼房挤着楼房,砖蹭着砖,岩石见不到,而绿意绝不是没有,不时见得水泥沙灰不严的罅隙处倔强的伸出一线草,这草生得多很特别,仙女般纤腰水中探月。树,也有,都被挤在仅有的三条街道上。矮矮的行道树夹街道贯穿南北,是拎网的绳,可它们太细,拎不起这县城,只成缝衣的线。 突然生出莫名的怅惘。 于是,想回去。 可同行的他们兴致正浓。无奈,只好还随他们吃力的爬。 |
游三峡(一) [随笔杂谈]
发表于:2012-11-08 阅读:10次
总迷恋幽美的风光,超然尘嚣之外的自然风景总摄我魂魄。不敢看郦道元的《三峡》,三峡的奇山绿水、秀木啸猿,让我恨不得扔掉一切,做三峡里的一脉溪,一茎草,一羽蝶,一尾猴。我害怕自己嚼过《三峡》后,没了人味儿,丢掉母亲孩子,疯了跑去。 可偏不期与三峡有了一次邂逅。 七月一日,我们九年级教师来到了三峡。 燕山号轮船,不停地打着闷吼,龟般慢吞吞的把我们驮到所谓的三峡。 当导游告诉我们三峡就要到时,我迅速跳下床,冲到一楼。 要与你最亲密接触了,我的三峡!就要一睹你迷人的容颜了,三峡!你,剑峰削壁吧?你,奇树遮天吧?你,水急涡激吧?三峡!你,该是粉红的睡莲?该是敛屏的孔雀?该是羞赧的西施?该是掩面的琵琶女?三峡,你是怎样的容颜啊?就把我拥进怀吧,三峡,我想亲吻你的肌肤,沐浴你的鼻息。就把我留在这儿吧,我会做翠鸟穿梭深藏的道道峡谷,轻跳深沉的片片树叶,撒下闪烁的碎玉。 还好,一楼站台上还没人。我是第一个得三峡的人了! 我领略久违的三峡了。 宽宽的水呈在眼前。这就是三峡?浑黄的水像谁刚趟过,没见得撼人心肺的激流,整个的,宽幕布样铺开,还抖动出片片的纹,活如黄鱼的鳞甲,不过,这鱼不是死鱼就是老鱼,不能闪金烁银。看上去,水在流动,可太慢,像特臃肿的胖子蹒跚着身子,也许是水太多,特别拥挤了吧,水,迈不开步子。 这就是三峡?哪有灵巧和气势! 山,像是盘古利斧劈下,挺胸立着。可,个个半秃顶,是一夜间都遭遇了鬼剃头?哪里“巚生怪柏,清荣峻茂”!也见绿,可这薄绿只让人觉得是哪位喝绿豆汤的小伙不小心倾了碗洒上去的。 山淌不下绿,淌下水也该别有情趣。而平平的峭壁板着脸,不高兴着灰白色。 “要是雨天就好了!”跟着下来的同事晓东说,“那样会有瀑布飞漱其间。” 也是,没悬泉,只能寄希望落雨了。急雨成瀑,必很壮观。今儿却没眼福,只有的是身福了。似火骄阳把我们做烧饼烤,岩上没飞下寒水,却飞下火光,我们飞下了汗水。衣服贴着身子,黏黏的,活如胶裹,异样难受。 老天把我们当不听话的孙大圣,做丹炼了。 山不管这些,还漠然如翁。水不管这些,还温文尔雅,款款走着。 款款走着的还有轮船,一艘艘轮船,或摆着一辆辆挨帮儿的货车,或堆着一丘丘酣睡的煤。船把身子深埋在或许还凉爽的水里,拨开游荡的塑料袋塑料碗花样繁多的烂鞋,向前划着,尾部喘着蓝黑色的气,嘟——嘟——,此起彼伏的抒发着史上纤夫才有的烦闷。我不觉以为,三峡怕就是这闷吼撕裂开的吧?长长的峡谷成了这轮船的大音箱了,声波入了人的骨髓,入了山的骨髓,入了小灌木的骨髓。 入骨髓的还有那刺鼻的油烟。 “还想做三峡人吗?”晓东问。 这问题也在我心里翻转多时了。 |
风波 [随笔杂谈]
发表于:2012-11-08 阅读:25次
肖欣正勾头吃饭,饭碗猛的从手中弹出,硬生生的盖向脸,米汤夹携着肉丝豆角瀑布样从脸到胸到酱灰白肚皮,整个的粉刷了一遍,豆角肉丝散花般撒了一大片。 “他妈个X!找死啊你”肖欣暴怒,雷声般吼叫。眼没睁开,稠米汤把眼刷胶样涂得光亮,几粒开花米屑有吸盘样挂在眼皮儿、睫毛上。 “日你姐,是哪个死孩儿?找死啊你!”他还不停的狠骂。右手流星样抓了一下眼,再两手搓了搓,又左食指刮抹了一下眼,眼才算睁开。这时他拳头已攥成石宝的流星锤,就要飞出。 可眼前不是他猜想的哪个横肉大汉。 邻居钱惠抖着李逵式的脸,两手掐腰,就在眼前。虽不是彪形大汉,可先天的壮男士才有的魁梧,加后天的富人家才培育出的大块肌肉,绝像山寨王。她怒冲冲的,像矗立的冷面巨石。 “X你妈,还骂人!叫你骂!”肖欣那一句刚骂完,刚看清是谁,钱惠又飞起一拳,结结实实的砸在肖欣的鼻子上,鲜血一下子滚出,像炼铁炉倾倒滚烫的铁水。肖欣有着鲁提辖拳下郑屠的感觉。 这下肖欣怒发冲冠了,提起榔头样的拳头正当钱惠胸口一拳,钱惠一个趔趄,舞台碎步般后退,倒向自家伫立的广告牌上。 钱惠可没弯过脖颈软过手,她手后推一下广告牌,冲向肖欣。 “还打你姑奶奶啦你!”钱惠边厮打边怒骂,这骂声绝像发怒的母狮。 女人有天生的武器,就是锋利的指甲和牙齿。有的男人就戏骂,说女人是穿山甲和黑熊直接进化来的。钱惠手指或许是钢针做的,只一下,肖欣的脸已六道小溪垂挂成小瀑布,肖欣年轻身体壮,血也涌的急,像是心脏把血液给煮沸了。 “我教你打你姑奶奶!”钱惠边挖边骂。 手挖是第一招式,接下去出第二招——嘴咬,可惜钱惠没虎牙,咬着肖欣的胳膊狠劲的撕拽,肉始终没掉一块,这笨劲,野狗见了会笑掉牙的。 国人最大的爱好就是喜欢看热闹,估计DNA测序,会比老外多个叫好奇的蛋白密码的。 这不,这惊心动魄酣畅淋漓的男女混合格斗一下子吸引了许多人。几乎每个门店门口都稀稀拉拉的站着人,有嫌看不真切的就围了上来。 在自己门口比武,当然不会单打一。首先是肖欣的老婆郝芳跑出来了。 只见丈夫满脸满膀子全是血,右手抓着钱惠的头发用力拽,钱惠像饿狼正狠咬着丈夫的左胳膊。 “弄啥弄啥啊!”郝芳声音急促尖利,像钢刀弹拨快弦。 说着郝芳已跑到了跟前,用力拉钱惠。 郝芳个儿不算矮,有着多数女孩儿不吃早晚饭,差点整天只喝水才打造出的好身材。虽然四十有五了,还风韵犹存,楚楚动人。不过,这样的人,少了肌肉,也少了力量。她怎么会拉得动才二十出头重量级的钱惠! “你这娘儿们咋恁铁!母老虎啊你。”郝芳缺手劲儿,可还不算缺嘴劲儿。 “我铁?我老虎?谁教他喃粪嘴胡说八道!” “他说啥了?” “问他!” “你说他啥了?”郝芳转向丈夫。 “冇啊。我会说她啥!” “冇?你妈个球,还不承认?”钱惠又伸右手要挖肖欣,肖欣哪会让她抓着,一下把她的手拨开,这利索和力度堪比少林退。 “午饭时,你兔娃儿对吴连说了啥?”钱惠质问。 吴连是个卖肉的屠夫,近六十岁,皮肤黝黑,像个炭截子。花白的头发很乱,似乎和灰蒙蒙的脸在造词,叫蓬头垢面。脸型长条状,或许是岁月缘故,脸部肌肉下垂,像司机下垂的胃。左眼没下眼皮,眼球被生生的暴露了一半,恐怖得小孩子见了他就哭。嘴虽不是八戒式,却也稍向前突起,嘴从没合过,下嘴唇耷拉着,成小簸箕,活像小推土机。吴连不是没一点优点,他个子不低,足有一米八,更大的优点就是他是男人身。 “她的店就是那卖肉的给开的,花了七八万呢。”人群里有人小声说。 “他天天集罢就来了。破三轮就停在门口。”又有人说。 “说啊,你龟孙说说,对吴连说了啥?”钱惠又追问。 “冇说啥啊!”肖欣继续辩解。 “冇?X你奶奶,还嘴拧!那为啥你们嘀咕了几句,他进屋就质问我又有谁了?” 钱惠的丈夫从里屋出来了,正要帮老婆,听到这句,脸一红,勾着头,又回到店里。接着,传来啪嗒一声重重的门响。 “冇,真的冇。” “那谁说了教他孩儿死完!教他一家儿人出门车轧死!” 这会儿,肖欣不吭声了,脸一下子成灰色,像断了电的幕布。 “说啊!你赖孙孩儿咋吭气儿了?驴屎蛋儿塞住嘴啦?憋死了?” “冇!我冇说!”肖欣又梗起了头,声音也提高了半度。 “你冇说?那是鳖娃儿说了!谁说了是王八蛋!教他得个孙儿冇屁股眼儿。”钱惠继续高着嗓门臭骂。 “俺冇说就是冇说!”肖欣还坚持着。 “还不承认啊你!好,我打电话。”钱惠松了手,掏出了手机,“吴连,过来!”声音斩钉截铁,“啥?你翻天了不是?别给我瞎找理由!你来不来?给我快点来!不来的话小心你的狗头!想教挂你的料桶啊你!再来别想再上——” 她话没说完,不知为啥,突然打住,转头往店里喊:“死X孩儿,给我滚出来,冇看你老娘被欺负吗?钻屋里干啥?死啦?” “叫老天爷来也不行!俺冇说还是冇说!”郝芳说话了,“你咋诬赖好人啊!”。 “好人?水里随便摸个都比他强。叫转圈儿人说说,学院学生他包过几个?在你楼上住的那妞是他的啥?” 钱惠还没说完,郝芳就跑回店里,接着,也听见啪嗒一声门响,再接着,就是嗷嗷的哭声。 之后的故事,不怎么惊险了,肖欣回屋里锁了门再也没出来,任钱惠拍打。大家耐着性子,看屠夫来了会有什么奇事发生,而饥饿的蚊子在身上打出密密麻麻的钻孔了,还没他的影儿。 听说后来钱惠接了个电话,钱惠骂:“车坏了,跑着来!你这驴砵的往日儿咋跑的恁快!” 再后来,没人知道了。只听说,有人后半夜起来还见两家的灯亮着。 |